《藝術教育》雜志封面報道南京藝術學院居其宏教授感人事跡
學術魅力與人格魅力的交輝
——記南京藝術學院教授、博士生導師居其宏
文章來源:《藝術教育》 2012年9月號(上半月刊)
◆ 倪振林 陳泓歷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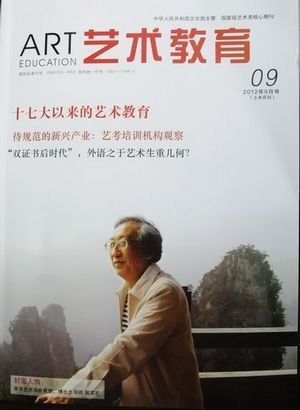
居其宏,音樂學家、評論家。1943年4月生于上海,1961年進入上海音樂學院附中,1969年本科畢業。1981年獲碩士學位,同年分配到中國藝術研究院音樂研究所。長期從事當代音樂研究及批評、歌劇音樂劇理論與評論、音樂美學研究,1994年被評為研究員。中國音樂家協會會員、中國音協理論委員會委員、中國音樂美學學會會員。現為南京藝術學院教授,音樂學研究所所長,南京藝術學院碩士生導師、博士生導師,南京藝術學院學報《音樂與表演》編委,《中國音樂學》編委、《中央音樂學院學報》編委。2010年受聘擔任北京大學歌劇研究院研究員。
在南京藝術學院的校園里,從書記校長到普通師生見到居其宏總會尊敬地稱呼聲“居老”。一聲“居老”,飽含著大家對他的尊重和敬仰,這除了因為他的年紀和在音樂學界崇高的學術地位外,更重要的是因為他那份對待教育事業的責任與奉獻,對待學術正義的堅守與捍衛和對待學術研究的嚴謹與執著,在這位老者身上,學術魅力與人格魅力的交輝相映,迸發出奪目的光芒。
“居氏輔導書”里的責任與奉獻
作為國內音樂學界的權威學者,居老的頭上自然少不了很多奪目的“光環”,然而和那些光鮮照人的職務、頭銜相比,居老最為看重的卻是一個最平凡不過的身份——“教師”。用居老的話說,“不管擔任什么職務,我首先是一名南藝教師,教書育人不但是我的本職,也是我認為最有意義的工作。”
自2002年正式調入南藝以來,居老已指導了14位博士生和5位音樂學方向碩士生,同時還擔任了11位音樂表演方向碩士生的論文指導教師。在研究生教學和論文寫作中,除了面授環節,多年來,居老一直堅持著以“輔導書”的形式,對每一位研究生的學位論文寫作進行一對一的書面輔導,而這一本本傾注無數心血的“輔導書”也成為了居老愛生敬業、傳道解惑的最好體現。
“長、細、準、透、嚴”,很多學生經常用這5個字來概括“居氏輔導書”的特點。
“長”,即篇幅長,每本輔導書無不是洋洋灑灑,字數最少的也在萬字以上,在南藝工作的10年里,輔導書的總篇幅已近70萬字;“細”,即批改細,從語句間的邏輯承接,到錯字病句,再到字體字號,即便是最細微的錯誤也逃不出居老的眼睛,就連文章中標點符號的錯誤也常被一一列出;“準”,即把脈準,不管學生的論文涉及音樂學的何種領域,篇幅多長,輔導書總能一語點破文章的“死穴”;“透”,即講得透,針對學生論文中的各類問題,居老總是會耐心地分析問題產生的原因,鞭辟入里、入木三分,同時幫助學生尋找解決問題的方法和途徑,提出修改完善的建議或方案;“嚴”,即要求嚴,在很多同學的輔導書中經常會看到類似這樣的話:“這段文字如此定稿已無大礙,但仍有進一步完善的可能,你不應該以這樣的標準要求自己,希望再加把勁,不要留遺憾。”
在眾多輔導書中,博士生王建的那一份或許最為特殊,這也是居老迄今為止“耗時最多、用力最猛”的一份輔導書,從這份長達5.3萬字的輔導書里,王建感受到了老師如同父親般的嚴格與慈愛。
讀書期間,王建和妻子都沒有穩定的經濟來源,夫妻兩人還有孩子要撫養。巨大的生活壓力使得王建意志消沉、常常借酒澆愁,博士論文的研究撰寫工作也受到了很大的影響。眼看著答辯日期日益臨近,居老的心里焦急萬分,他擔心的是,如果延期答辯,王建的工作就很難落實,一家三口還將度過一年清苦的日子,他說:“作為你的導師,我實在不忍看到這樣的情況發生。”然而,即便如此,對論文質量,居老卻沒有絲毫放松要求。
王建的論文初稿完成的那天,正在參加中國音協新春聯誼會的居老,因為對論文放不下心不得不中途退場,剛回到家便馬上開始閱讀論文并寫作輔導書。經過了連續10天的伏案工作,年近古稀的居老已是疲憊不堪。在輔導書中,居老對論文進行了逐段評閱,列出來的修改意見多達120條。在輔導書的結語中,一段父親般的教誨讓王建每每想到都會心緒難平——“作為你的導師,每聽及此(借酒澆愁、自暴自棄),在同樣為你痛苦而擔心的同時,我也想告訴你,這不是一個意志堅定、性格剛強的爺兒們在面臨人生挫折時該做的事情、該有的作為……我要求你:必須堅決、干凈、徹底地排除那些不爭氣的心態和做法,立即振作精神。我相信,在你我師生的彼此默契配合、共同努力奮斗之下,這篇論文是有希望修改好的。”
在一本本輔導書的字里行間,老師對學生的那份責任和奉獻,體現在很多不經意的細節之中。2010年的寒假前,李潔完成了碩士論文的初稿,沒想到僅僅一個星期后,一份兩萬多字的輔導書便發了過來,居老要求她放棄春節休假抓緊時間修改。這樣的要求似乎有點不盡人情,然而當李潔無意間看到輔導書“2011年2月2日大年夜”的落款時間時,之前的抱怨隨即被深深的感動所替代。在隨后的一份輔導書中,居老寫下了這樣一段話,“這個春節和寒假讓你在修改學位論文的緊張忙碌中度過了。這看來有些殘酷,但我們既然選擇了音樂學這門職業,便注定與鮮花、掌聲、熱鬧、富有、光鮮等等無緣,而只能以孤獨、枯躁、冷寂、清苦等等作伴;若在這行干久了,也就不以為苦,反以為樂矣。”
學術誠信前的執著與堅守
教書育人也好,著書立學也罷,“誠信”始終是一條不能跨越的道德底線,這也是居老為人、為師、為學一直嚴格遵循的基本原則。在他看來,“那些急功近利者、弄虛作假者的抄襲剽竊之舉、欺世盜名之作,除了徒增學術垃圾、造成出版資源和閱讀資源的無端浪費之外,更重要的是腐蝕學者靈魂,消解學術道德,助長投機取巧的風氣,因此更有必要運用學術批評的手段進行揭露。”
從2000年公開發表了第一篇學術反腐文章以來,面對音樂學界出現的各種學術不端現象,居老化筆為劍,堅定地扛起了學術反腐的大旗。至今為止,他先后在《人民音樂》《中國音樂學》等雜志上發表了十余篇文章,弘揚學術誠信,倡導“明學理、正是非”的學術氛圍。
也正是因為這份對學術誠信的捍衛與堅持,2008年的一場“退會風波”讓居老成為了學界關注的焦點。
當時的居老在國內音樂評論界一家重要的學會里擔任副會長。一次,該學會在決定是否發表揭露某音樂學院領導涉嫌抄襲一文時,沒有依據理事投票的結果,僅因學會主要負責人的“一票否決”就使得這篇文章沒能發表。事后,居老向學會提交了《退會申明》并在其博客中寫了一篇題為《學術腐敗:沒有贏家的賭場》的文章,以此表明一個學者在反對學術腐敗上不屈從、不妥協的人格立場。
此事件在國內音樂學界掀起了不小的風浪,一時間,不少學者紛紛著文為學術正義搖旗吶喊,有位學者在文章中這樣寫道:“是什么讓您對‘音樂界的學術反腐前景依然樂觀’呢?顯然不是事實,而只是一種‘邪不壓正’的信念。而在‘沒有贏家的賭場’中,其實也包括了帶著這種信念干預‘賭場’的人。”
對待學術界的學術腐敗現象,居老是深惡痛絕的,而對自己的學生,他的眼里更是揉不進一丁點的沙子。
“若要人不知,除非己莫為”,這是居老對學生們說的最多的一句話。多年來,學生們經常會聽到老師用這樣的比喻來告誡自己:學術造假行為實際上是造假者在自己的學術道路上埋下一顆“不定時炸彈”。這顆炸彈究竟何時起爆, 造假者茫然不知,只能為此惶惶不可終日。然而炸彈一旦引爆,造假者的學術聲譽便會葬送于轟然一聲的巨響之中。而一旦他的學生中有投機取巧、悖于學術誠信的行為,必然會遭致居老嚴肅的批評。
曾經有一位博士生在寫作學位論文時,將網上“蕩”來的幾段文字直接“粘貼”到了自己的文章里,本以為十多萬字的文章,這點小瑕疵很難被人發現,即便發現了也無傷大雅。但他的“小聰明”還是沒有逃得過居老的眼睛。隨后,憤怒的居老在給該生的“輔導書”里留下了如下幾段話:
這種連本科生都能一眼看出的小伎倆和小把戲,除了坑害你自己之外,又能糊弄得了誰呢?你的導師是吃素的?答辯委員會的博導們都是傻子?即便我們這些人眼睛都瞎了,學術良心給狗吃了,廣大人民群眾的眼睛可是雪亮的!來日肯定要將此文掛在網上,不僅是你本人,就連導師和所有答辯委員以及整個南藝音樂學的博士學位教學,都將顏面丟盡!
……
再一次嚴肅提醒你:學術研究是一個清苦、孤寂的事業,需要踏踏實實、老老實實、刻苦鉆研、科學嚴謹的學風,決不允許偷奸耍滑,投機取巧;故而,此病若不根治,不僅這篇論文不能提交答辯,你今后的學術生涯必然會出更大的紕漏——我先把話撂在這兒,日后勿謂言之不預。
學術研究中的嚴謹與執著
作為我國音樂批評方面的刀鋒手,居老敏銳的眼光、犀利的文風、和勇往直前、始終如一的個性,吸引著許多慕名學子。不光是在南京藝術學院,在北京和上海的音樂學府里,都流傳著這樣一句話——“如果就讀音樂批評專業的學生拿到學位時,卻不知道居其宏老師,真是一件很丟臉很失敗的事。因為如果不了解居其宏,就等于并不了解中國當代音樂批評。”
音樂批評是居老鐘愛一生的事業,在他看來,學術界如果少了爭鳴的聲音,少了批評的鼓號,必將會成為一潭死水而不斷腐臭。“用‘有容乃大’的胸懷,追求‘和而不同’的境界”,帶著這份學術理想和對事業的執著,居老從事科研工作數十年來筆耕不輟、立言不止,在國內各種報刊上發表論文和評論300余篇,出版了學術專著10余部、論文集10本,因其深度的學術觀點和嚴謹學術風格,受到了學界同行的廣泛好評。
“嚴謹、嚴謹、再嚴謹”,無論是在教學還是在研究中,這樣的態度始終被居老恪守。他的本行是歌劇和音樂劇的史論研究,后來是當代音樂研究。至于目前他最有發言權的音樂批評,居老開玩笑地說:“其實也是客觀形勢所逼,是被逼到這個崗位上來了。”
在居老奠定人生觀與學術觀的青春時期,他目睹了很多音樂家的坎坷命運。當時正處在文化大革命時期,音樂批評的攻擊很大,一些人把音樂批評當做政治斗爭的工具,一大批非常優秀的音樂家被打成右派,這給我國的音樂創作、音樂表演、音樂學術研究造成了很大的傷害。改革開放初期,血氣方剛的居老撰文提出了音樂發展要在“不脫離政治的前提下,淡化政治”的主張,認為音樂不應過于趨于政治化,成為意識形態化的“單一武器論”。此論一出,立即在學界引起爭鳴。
在學生眼中,老師的底蘊深厚、文字犀利,他的學術成就,往往是后輩晚生們追索仰望的高峰。居老一直告誡學生:“很多人認為音樂批評只能是吹喇叭抬轎子,只能說好不能說壞,這是我絕對不允許的,批評家作為獨立人格,應該有自己獨立的判斷標準和喜好,可以是主觀的錯誤,但是不能不發出自己的聲音。批評家不能指導實踐,他們是間接地良性互動關系,彼此影響,彼此支持。策略因人而異。”
嚴謹、執著、認真、直率,這就是居其宏,一位閃爍著智慧光芒的仁者和智者。(文中王建、李潔為化名)
更多有關"學術,音樂,輔導書,批評,論文"的文章請點擊進入南京藝術學院新聞中心查看

